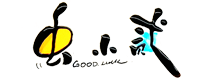听见年光的剥落声
年关的脚步,每每是猝不及防的。腊月廿三的黄昏里,爆竹声突然在楼宇间炸响,像莽撞的客人提前叩门,惊得我心头一颤。这声音,仿佛在宣告:年,又来了。
年关的滋味,是浓烈而喧嚣的。超市里,贺岁歌曲一遍遍循环播放,欢快得近乎单调,仿佛要榨干人最后一点气力。人们推着购物车,脸上却浮着一种甜蜜的疲劳,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间穿梭,如同在一条拥挤的河道里漂流。我站在其中,竟有些茫然无措,仿佛被这汹涌的节庆洪流裹挟着,身不由己向前,却不知何处是岸。这热闹的洪流,竟也冲不散心底悄然升起的孤寂。
城市在年关的催促下,也悄然换了容颜,街巷里骤然冒出许多卖春联、灯笼的小摊,红彤彤一片铺陈开来,映着行人匆匆的脚步。菜市场里更是人声鼎沸,鸡鸭鱼肉,各色的菜蔬,堆叠成山,人们挤挤挨挨,在讨价还价声中,在时间的河床里淘洗着年货。我挤在人群里,听着那些熟悉的乡音,看着那些被岁月刻下深深印痕的脸庞,他们仿佛在年关的洪流里,奋力打捞着某种即将沉没的、属于旧日时光的温暖。这喧闹的市声,竟也冲不散心底悄然升起的孤寂。
年关也成了旧友重聚的时节。昔日同窗,如今各自奔波,难得一聚,却总有些微妙的生疏。大家围坐,彼此递烟的手势过于熟练,寒暄的话语也像排练好的台词,在空气中飘荡,却难以真正抵达彼此的心底。我望着他们,仿佛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,彼此的面容清晰可见,却无法触摸到对方真实的温度。这层薄冰之下,是各自奔流的生活轨迹,早已在无声中分岔远去。酒杯在手中传递,碰出清脆的声响,却碰不碎那层无形的隔膜。我们谈着近况,说着笑话,可那笑声里,总带着几分刻意,几分试探。那些被生活磨砺得圆滑的棱角,那些被岁月掩埋的锋芒,在年关的灯火下无处遁形,却又被小心翼翼地藏起。我们举杯,饮下的仿佛是时光酿成的涩酒,在喉头滚过,留下微凉的余味,提醒着彼此,我们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可以赤诚相对、毫无顾忌的少年了。
年关的惆怅,最是浓烈地缠绕在母亲身上。母亲总在年关临近时染发,我偶然瞥见染发剂下新露出的白发,如初雪般刺眼。她察觉我的目光,慌忙笨拙地遮掩,动作里竟透出几分少女般的羞怯。我心头猛地一酸,却只能装作未见,轻轻上前拥抱她。那染发剂刺鼻的气味,竟也成了我心头最深的酸楚——原来时间这贼,早已悄悄染白了她鬓角,又偷走了她多少青春,只留下这化学的香气作为遮掩的凭证。
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,是年关最恒定的风景。她系着那条用了多年的旧围裙,在氤氲的蒸汽里,在灶火的跳跃中,像一位虔诚的祭司,准备着一年一度最隆重的献祭。锅碗瓢盆的叮当声,是她献给岁月的祷歌。我站在厨房门口,看她专注地揉面、擀皮、包馅,那动作里沉淀着几十年的光阴,也沉淀着一种近乎执拗的温柔。那香气,是家的魂魄,是时间无法完全偷走的凭证。她对着镜子涂抹染发膏的样子,像在与时间谈判的战士,笨拙而顽强地守护着一点青春的残影,那刺鼻的气味,是抵抗无声流逝时最悲壮的硝烟。
除夕夜,爆竹声此起彼伏,震耳欲聋,仿佛要撕裂这沉沉的夜幕,宣告新年的到来。我独自立于窗前,看窗外烟花绚烂绽放,又瞬间凋零,如一场盛大的集体狂欢。然而,当喧嚣散尽,万籁俱寂,一种更深沉的孤独却悄然袭来。这孤独并非源于无人相伴,而是源于对生命流逝的清醒凝视:年关如一道门槛,跨过去,我们便又向衰老与终点迈近一步。
儿时的除夕,守岁是件大事。一家人围炉而坐,嗑着瓜子,剥着花生,听长辈们讲古。窗外是零星的爆竹声,屋内是昏黄的灯光,映着墙上新贴的年画,空气里弥漫着油炸点心和冻秋梨的清甜。那时总觉得夜很长,长到足以装下所有对未来的憧憬。如今守岁,灯火通明,电视里喧嚣着跨年晚会,窗外是连绵不断的烟花轰鸣,可心却像被掏空了一角。那炉火的暖意,那昏黄灯下的絮语,那冻梨的清甜,都成了记忆深处模糊的底片。时间带走了什么,又在年关的喧嚣里,加倍地偿还给我们一种名为“失去”的清醒。
年关的喧嚣与热闹,终将如烟花般散去。当所有祝福语都飘散之后,那被年关放大的孤独与惆怅,反而沉淀为生命最本真的底色。年关的喧嚣,不过是年复一年在时间河床之上浮泛的泡沫;泡沫终将破碎,而沉潜于河底的,是生命本身那无可回避的孤寂与流逝的真相——这真相,在年关的喧闹里,反而被映照得格外清晰。
原来年关的惆怅,并非无病呻吟,而是生命在时间刻度上,刻下的一道道真实而深刻的印记。这印记,在年复一年的喧嚣与沉寂中,愈发清晰,提醒我们:生命是一场盛大的奔赴,而年关,不过是途中那一声悠长而必然的叹息。
除特别声明为原创作品以外,本站有部分文章、数据、图片来自互联网,一切转载作品其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。
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。邮箱:116169014@qq.com
上一篇:长歌当哭,醉是人间四月天